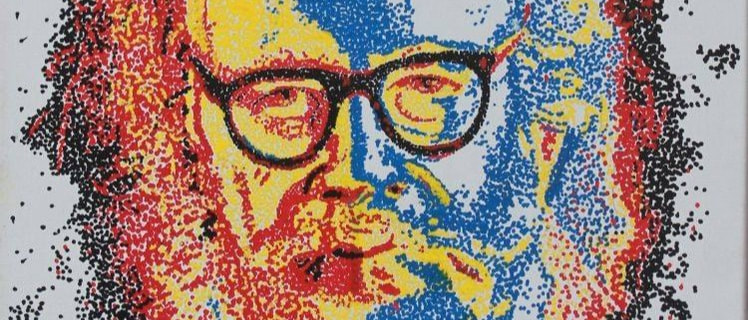葛羅托斯基致研討班畢業生的演說
Farewell Speech to the Pupils
校譯:黃家駒,完成於2019年9月9日
【下文是根據一個大約在劇場實驗室(Laboratory Theatre, 1969)成立十周年時,一個於歐洲的國際研討會內容抄寫出來。參加研討會的是很多聲稱「根據Grotowski在工作」的人和團體(Attending the seminar were many people and groups who claimed to work “according to Grotowski”.)】
有一個問題擺在了我們面前:你們覺得訓練可以引領向創作的方向嗎?你們堅信訓練可以在創造中找到它的用途嗎?在我看來,這是關鍵性的問題。我想,如果我們像四散的兔子一樣,行進在各自的方向上,奔向不同的主題,那我們就不會找到任何答案。人們不可能總是回避關鍵性問題。
如果我們覺得一個人不應該去評價和分析其他人的作品,那麼討論也就不可能存在了。也許有人認為,只有我才有權利進行分析。這就意味著某人有著專權(monopoly)。但,第一,誰也不具有這種專權;第二,即使某人在某段時期具有某種專權,那也只是階段性的如果有人認為,這樣的一個研討會無須得出什麼結論,所以不應該評價其他人的作品——這對參與者來說是很舒服的,但這麼我們就僅僅像兒童一般玩耍了一番、玩完就算。
所以無論如何我都堅持一點,即每個人都有義務要成為「篡奪者」(usurper),總及都要對所見事物作出回應。就因為我們是活著的,所以我們對事物會有興趣或者感到厭倦、要不就被感到吸引或抗拒。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或許我們這裡無人有權來言說,那這整個研討會的一切也就毫無意義;又或許,我們每個人都有相同的言說權利並且在某程度上需要履行言說的義務。我的意思不是說要大家展開相互間的攻擊,向所作的評論必須要尖銳,縱使我自己的言談也不太顧及顏面……好吧,如果我們有一些需要,如果我們在追尋著一些切實的東西,如果我們不是要當個滑頭,我們就應該說出哪些東西吸引著我、哪些東西讓我厭惡。
我們都知道,我們在此所作的練習並沒發展至最後「成品」(products)的階段。但我們可以看到種子在某處發芽了,驅動力(impulse)在某處形成了,營養在某處豐富了。或者完全相反,這裡令人窒息,缺乏孕育成果的土壤。這不是一個「忠於某個體系」的問題,問題在於,「真理的種子」或者說「戲劇實相的種子」(seed of a theatre of truth)出現了嗎?這是唯一的問題,因為「體系」本身毫無意義。
X女士提出了一個滑稽而有趣的問題:「我們這裡看到的一切與葛羅托斯基先生的作品有關係嗎?」這個問題引起了我的注意。但這個問題在這裡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種子在哪裡?只有弄清楚這一點,我們才能去追問你們所說的「葛羅托斯基體系」是造就了貧瘠還是孕育著活力?然而這第二個問題同樣使我疑惑,因為我並不認為我有這樣一個「體系」……
首先,不存在一個「葛羅托斯基體系」。其次,這裡沒人在依隨著我的精神進行工作。跟不跟隨我的精神工作又有什麼重要呢?沒關係。我一直對不按照我的精神來工作的人更為尊敬。事實上,按照我的精神工作的人其實是在遵照他自己的精神去工作。沒人能以我的方式工作,因為每個人都是不同的。Y女士提起的這個問題是我一開始就想向大家闡明的。只有在這樣一種觀念中,我們才可能找到「方法」(method):以坦誠的、非模仿的、不躲閃的、不走捷徑的方式去工作;去走近演員,全身心地走近他,以你的全然存在;一直到忘記你自己,同時期望對方和你一樣,和他相遇。這樣的狀態在我們當中發生了嗎?這對我來說是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將對此作出分析。
為什麼我們的討論如此令人悲傷?我看到了很多神學的、教條式的論說,以及訓練。還出現了一些哲學概念的元素。我也聽到了一些帶有神秘性、陰暗色彩的討論內容。但你們卻沒有顯示出足夠的勇氣直截了當地說出自己的感受。真實的聲音很少,只有籠統的腔調:怎麼樣避免與事實衝突?如何避免觀念與事實、期望與事實、理論與事實之間的衝突?那麼,尊重是什麼?我很清楚尊重有很多的刻板形象,包括稱呼他人的名、花言巧語、說些漂亮話、在一張桌子上用餐、談論著我們為何悲傷(因為「我父親去世了」、「我和女朋友之間出了點問題」等等)、以極大的興趣傾聽著這一切、傾聽著某人談論著他的病情或是他的工作。這一切都製造出一種氣氛。經常性地,哪裡存在著虛偽,哪裡就有氣氛。同樣的,當有人在談論氣氛,那兒必定存在著虛偽。這我們讓自己浸沉在這種溫水環境中……「親愛的約翰」、「親愛的法蘭西斯」、「我們倆多要好啊」、「真友善啊」、「你我之間沒有任何距離」……而我對於「尊重」的理解與這些截然不同。
在這個研討會上,我對他人的尊重體現在我把每天的所思所想記錄在筆記本上。我記下來,並不是計畫把它們全部告訴你們。我用的是非常個人化的語言,毫不隱晦自己的真實想法。但現在我決定要將這些筆記一頁一頁地讀給你們聽。我不針對什麼具體的事情,我是想給大家展現出我的尊重。尊重,存在於勇敢的坦誠中。我可能並不正確,但我有義務保持坦誠。
也許這會引起一些不快,但我將很坦誠。
這將是一段獨白。這並不是因為我不想回答你們的問題,也不是因為我不想聽到反對的聲音。我不想從某種「體系」的角度來展開討論,我也不想從我的工作方式出發來展開討論。我只想讀出自己記下的所思所想——這些記錄是我的感受,涉及到你們工作中所有促發我思考這個職業的部分。
這將不是很有條理的發言。有條理的演說已經夠多了,人們很快就會把這種演說的內容當作教義來對待。而我有的只是筆記。
我將會像是一個幽靈般和你們在一起,就好像某個人既在場又不在場。如同一場葬禮上的頌歌,這就像是和你們的一場告別。我馬上開始。
有人講,我們在這裡運用了「放鬆,就是冥想」。這樣的說法毫無意義,這如同說「我做體操,就是在寫論文。」你要麼是說錯了,要麼沒有作放鬆而在做其他事,要麼沒有作沉思而是在做另外的事。無論如何,語言有著界定好的意義範圍。「放鬆」(relaxation)一詞並沒有深長的歷史,但「冥想」(meditation)一詞的歷史則很長……
我要求大家給我的是具體的答案,而不是謎一樣的回答。前面的時間,你們帶著謎一樣答案在兜圈子沒人對事情的必要性、豐富性發表過明確意見;沒人明確說我們是在作真正的訓練還是在對訓練進行拙劣的模仿(parody),沒人指出這裡的動作(performance)是表演(performance)或者僅僅是對表演的拙劣模仿?
當你們討論一件具體的事情——比如「放鬆」時,至少要做到明確。因為,當我聽說這個小組或那個小組每天花兩三個小時練習「放鬆」——「放鬆,就是冥想」,人們這樣歸納——我感覺自己就像是在瘋人院。
有時候我會提到西藏、印度、波斯以及「神秘的體系」。我似乎可以被指控是對東方世界情有獨鍾——這不僅僅體現在我的旅行經歷中,也體現在我練習所使用的瑜伽元素中。但我提議,在不將自己與他者文化隔絕的情況下,我們應以自身為歸宿點來尋找答案。因為,如果你尋找的答案只是在他處非常重要,而不是對你自己具有重要性,那你就會陷入幻景之中。你的追尋,僅僅是為自己尋求藉口。你可以學習遠方的、久遠的體系,你可以從中吸收一些元素,只要你對相關體系有足夠瞭解、能夠在你自己的語境中賦予這些元素以恰當的意義。但追尋某種「奇跡性的答案」(miraculous solutions)是不可取的。我再重複一遍:所有這些「神秘的國度」僅僅讓我們可以可以在其中找到自身資源的反射;那種追尋「奇跡」的欲望在某種程度上是對大家的毒害。
我們沒有足夠的真誠去走自己的路。我們尋找避難所,尋找躲藏之處。這就是為什麼我們的訓練,不是走向一團混亂,就是變成健身運動。這建基於我們的傳統——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建基於我們的弱點。於是,你們或者僅僅作出本能的自然反應,然後就導致一團混亂;或者就只是知道展現熟練的技巧,然後那種機械化的反應機制就啟動。我在此必須說明,我對此毫無責任,鼓勵人們尋找避難所的不是我。準確地說,有的人隱藏在混沌之中,有的人則以被馴化而隱藏自我。因為這是簡單易行的。
在練習中可以發現很多不同的細節,但篩選和理順出正確的要點卻要很多年。當發現了一個連接完好的圓圈後,我們不應停步,而要繼續尋找這個圓圈的內在統一性。關鍵在於,林林總總的細節不是最重要的,細節之間的內在聯繫才是最具活力的。我能想到很多細節,和我們所運用的不同,它們不是最好的。重要的是,細節之間的次序不是隨意的、偶然的。我們在這一展開的領域——精確性和自然反應相結合的領域——中所進行的探索才是關鍵性的。
另外一點:我不明白為什麼在你們的練習中,帶領者會中斷演員的練習,在演員的開始進入真實的那一刻進行干預?帶領者在角落中或舞臺周圍說些什麼,這是絕不應該做的事情。導演( director)或帶領者( instructor)必須知道干預的時機。如果演員在開始時就走錯了方向,這時可以阻止他。但若演員已經開始並逐漸接近他表演的高潮,導演就沒有權力來干擾他。導演必須等待,直到演員完成一段,完成了某一段的高潮部分,他才可以說「停」。導演和演員之間存在著某種君子協定:在排練中,當演員正在表演,接收到導演給他的一些指示,此時演員不應離開自己的表演進程,不應轉換到私下模式(private mode)中。他應該繼續自己的進程,同時聽著導演的指示。這就是為什麼導演只應該說一句或最多兩句很簡短的指示,因為這樣他才不會干擾演員。演員聽到指示後應立即延續自己的表演,因為如果他就此丟棄了他的表演線索、徹底放棄了他的進度,如果他轉換到私下模式去回答導演說「是的,你是對的」或提問「你在說什麼?」,那麼前面的整個作品排練就都白費了。
導演如果說起話來,說了很多,會很容易中斷演員的進程。導演只應說必要的事情:不是描述、不是命令,而應是一種呼籲、一種刺激——僅此而已。導演不應為演員預設任何事情。他的常識應告訴他自己,給演員的創造提供可能性空間,為演員提供足夠的動力。還有,導演絕不應容忍自己或演員假裝工作。練習當中應一視同仁。有這樣一種人們所說的「導演的智慧」。當帶領者自己也開始進入工作,或是和其他人一道練習,他應該堅持到底,特別是當這是一段現場展現(presentation)時。帶領者沒有權力站在圈外命令他人「快一點,做,快點」,然後過一會跳進來和大家做幾分鐘練習,接著又跳出去繼續發號施令「做呀,別假裝,做」。如果帶領者希望腳踏實地一點的話,他應該和演員們站在一起,和他們一起勞動,直至揮汗如雨方知疲倦。如果他一直站在圈外,他在演員們工作的時候就不應該說話。演員們完成時,他才可以發表意見。我想如果是導演參加到練習中來,他就不應該比別人做的少些,而應該多些。在其他人休息的時候,他可以和某個演員一對一地進行工作,然後換一個人——其他人繼續休息,以此類推。
在導演和帶領者之間存在著一種差別。導演站在圈外並在練習結束後提出一些必要的意見,帶領者則可以由演員中的一人來擔任。如果練習缺少了些什麼,帶領者可以在幾分鐘之後介入,他不能在整個進程全部結束之後再告訴演員們他們全做錯了、必須重頭再來一遍。這樣的處置方式如同懲罰。
而且,誰也不能給工作中的他人強加上一種節奏。帶領者可以試著強加某種節奏,但前提是,他自己啟動了一個工作進程並試圖刺激這個進程中的其他人。也就是說,他把自己的工作節奏強加給了演員,希望自己的節奏得到實現。但一般來講,練習中的節奏應自由流動在每個演員之間,包括節奏的變化、細節的轉換方式等,都是如此。然而,有的時候節奏需要帶領者來負責,那就是能量需要得到調節的時候。帶領者應當知道如何創造出多樣的可能性,使人們真正地而非假裝地去工作,同時又不感到痛苦。如果某人在開始時工作力度過大,那他不久便會尋找其他節奏。因為當演員假裝表演或不願付出真正的努力時,他就應該要刻意用力地工作,甚至顯得有些殘酷地要他用力工作。在帶領者要求真實的表演,而演員作出回應但又不能作自我調節保護時,帶領者就有責任以合理方式來調節能量。
帶領者永遠不應把練習當作是他自己權力的展現,即便是無意識的也不行。導演應該知道,最好的情況是,在訓練現場他本人根本就無須出現。有一些最好的導演時常在排練中長時間地保持沉默,因為完全沒必要去說些什麼。
在訓練中能探索出什麼樣深邃的東西?在還沒有達到創造性活動的訓練中……就只有一點:尋求「改進」。
這裡有些人說,在訓練中沒有安排時間進行討論。哦,是啊!我能理解:為了得到外在的滿足,你們仍然需要得到讚賞,讚賞你們參加了意見、概念等等的學術交流中。史坦尼斯拉夫斯基曾分析過演員的這種需要。在他的最後一部作品Tartuffe中,他說:「請注意,在第二次、第三次排練中,表達出最華麗的概念的演員將是作品中最無能、最貧乏、最偷懶的。」為什麼?因為在概念上喋喋不休就是為了躲避訓練。
最初幾天的訓練後,你們曾自己組織了一次討論,當時因為時間不早了,很多人都躺在地板上。我注意到了一些事情。你們躺的方式是怎樣的?我將嚴格地宣讀我的筆記:「他們躺的方式是怎樣的?他們躺著以表示他們在放鬆。他們把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到自己身上,眼睛盯著腹部處的衣服扣子。他們對於互相之間缺乏交流感到疑惑。他們‘表演’著交流,但他們並沒在交流,因為他們都以自我為中心。他們躺臥的方向如何?就好像是要遠離他人。他們以嬰兒的姿態躺著,有些人採取不同的姿勢。我想這是因為他們真的累了,而他們躺著時正是唯一沒有令我感到干擾的時候。因為他們向這邊躺著,他們在聆聽。即使他們躺著,我能夠感覺到他們。」
在關於人際關係的探索討論中,我經常聽見「打開」( opening )一詞。這個詞聽起來很熟悉。在我們的訓練中也常聽到這個詞,但事實上我們沒有做到「打開」。因為「打開」從「真誠」中來。
「真誠」意味著「打開」。在生活中,我們會在有安全感的情境中向同伴「打開」。要在訓練中找到安全感是很難的。悖論在於,我們對人際關係所作的外在形式不能產生安全感。不但如此,安全感本身也不是最終目的。我們就像是大樹,應該開花結果。所以那種能誕生成果的相遇才是重點。從我的經驗來說,當一個人知道每個小組成員都忠實於對方時,安全感就產生了;當我們可笑的一面、容易引起流言蜚語的一面不被他人私下評論或嘲笑,人們就可以在真誠中找到安全感。一旦有人對集體工作的基本原則表示尊崇,成員之間的相互忠實就逐步形成了。沒有這些基本原則,工作中將只有緊繃的關係,要求某人去做他沒興趣做的事情,就會被視作為一種侵犯。
但當有了義務關係,要求某人工作就不會立刻被視為攻擊,因為成員之間有了某些約定和義務。集體工作中的這些規則可能顯得比較嚴酷,但事實上它們並不嚴酷,它們創造出一種約定。這種約定不是產生於壓制,壓制產生不出這樣的東西。這是一種雙向選擇。其中包含著一種決定:如果你不願意工作,你可以離開。這是基本要求。在團隊中,沒有人是被羈押的,大門向每一個人敞開。如果我的同事們不能接受我了,我會走出去,同樣,如果有同事不再能接受我和其他同事,那他自己也會離開。這很自然,這是自由的選擇。但你不能作出一個選擇卻又不遵守義務,這就不誠實了。
我想回到已經討論了很多的「神奇的國家」這個話題上來。印度的一些文本提出,最重要的事之一是建立一個空間,「一個人必須得有個房間。」如果你沒有房間,你得有一處沒有其他任何用途的地方。它可以是一個山洞,或是一個能讓你感到與世隔絕的樹林。當你想要工作,你要到那裡去。在那裡,你需要回避所有其他的活動。通過這種方式,你節約了很多能量,因為在這樣一種場域中會為我們帶來所需的專注力。從巴甫洛夫( Pavlov)的理論出發,這也是可以理解的——這就是一種條件性的反射。最後我完全同意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空間運用觀。他常說任何一個道具都不應有私人用途。比如說,在休息的時候,你不能用劇中的道具杯子來喝咖啡,如果你用了,有些東西就會消失。在史坦尼的時代,劇院是貧窮的,演員們穿著他們自己的衣服進行演出。所以史坦尼斯拉夫斯基——他絕不是個神秘主義者——曾試著推行一種儲放戲服的方法。他在「倫理學」(Ethics)中對此的描述很有趣,從實用的角度說又是非常有道理的。當你把自己的外套掛在衣櫥裡,僅在演出時才穿上,這衣服就給你帶來了一種非同尋常的價值。它不再是你個人的外套。所有這些細節,都是我們職業的組成部分。
有人問,戲劇中的人生和現實中的人生有何關係?這個問題假設著生活劇團(Living Theatre)比較接近於我對這個問題的處理,因為生活劇團的成員們將生活和戲劇統一在一起,不將二者割裂開來。生活劇團是個特殊的例子。你不能指責他們沒有為理想作出犧牲。他們說,人不應佔有任何事物,他們也確實一無所有;他們說,應該做一個流浪者,而他們確實一直在奔走;他們說,應該以做愛的方式去搞革命,他們也照此履行。他們言行一致,所以我尊重他們。但我不把他們視為我的專業上的伙伴,因為我的專業是劇場(Theatre),生活劇場的專業是流浪(wandering)。
我說的「專業」,是指什麼?對於我,它是一個婚禮的會場,也是生活中的一個地方。戲劇內外的生活究竟有什麼聯繫呢?實驗劇院( Laboratory Theatre)之外的波蘭演員們,特別是那些與我們不算是朋友、選擇其他戲劇類型的演員,一般把我們劇團看作是一個家庭或一個修道院。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是一個家庭?通常的回答是:「因為你們總在一起,因為你們都是朋友。」如果我們問為什麼是一個修道院?通常的回答是:「因為你們把自己封閉在工作中。」如果我們進一步問,這是否意味著我們不參與生活、不經歷生活的鬥爭?回答恰恰是相反的。只能說我們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我們的表演上。
外界的這些評論都是不真實的。欲近之,先遠之;欲見之,先離之。當我們抵達弗羅茨瓦夫(Wroclaw)的時候,市長把我們的住處安排在同一幢樓裡。但我請市長把我們的房間分散到不同的樓裡邊去。大家不能總是待在一塊兒,要不然,你的感覺就全沒了。鄰居之間產生的衝突和私人事務將和工作混雜在一起。然而,我們的確是經常串門。當有人邀請我,我就去他那裡,然後開個會。但如果我們一直是鄰居,並且工作的時候還必須相見,那就必然導致空洞和無聊。我們團體裡差不多每一個成員都有家庭,都有妻子兒女。每個人都會遇到問題,有些是很難的問題。當我遇到問題,我不會隨便找一個人來求助,而是去找一個同事,一個很要好的同事。排練與此不同,史坦尼斯拉夫斯基的《倫理學》(Ethics)對此有所討論:「你來到劇院,你就必須把你生活中那雙高筒靴留在門外。」因為,如果有人遇到問題——我們都會遇到問題,每天都會有人遇到難題——而把大家都牽扯到他的個人事務中,他也就無法從他的私人問題中解脫出來。他只會將自己的緊張傳遞給大家,只會增加團體的緊張感。但如果反過來,你來到劇場,在此迎接你的是另一套義務關係,沒人會打擾你,大家會和你團結在一起,你期待著自己的真誠,你開始工作——此時的焦慮就會減輕。也許排練結束後焦慮會捲土重來,但排練或許能帶來收穫——你可能會得到一個新視角、一種不同的心態。在你所在之處,全身心地投入。
我在這裡,在排練中,就要全身心投入。因為如果在工作中我還惦記著家事,就將產生一種尷尬的混淆。如果在工作中,我完全付出,於是我的日常生活隱退了。過後,我將能夠以更好的方式來思考事情。席勒(Schiller)曾說,藝術中的鮮活的事物需在現實中消亡。我對這句話有自己的理解:人們在創造性的藝術中呈現的,不能是某種瑣碎的、平常的、日常性的事。比如,如果你在進行愛情情節的練習,你所有的愛情經驗、所有屬於愛情的時刻、那些最重要的愛情時刻都會展現出來。但假設你剛剛戀愛了兩個星期,就想立即表演出來,那決不會是富有創造性的。首先,你將使自己的愛情降格與解體;你將費盡心思來剝削(exploit)你的愛情經驗。其次,你將在工作中製造一種含混:假設你很愛那個人,但你又想在練習中証實這一點。這是一個危險的轉向。我不是說,我們沒有權力將還在進行著的事件展示出來。我以一個例子來解釋我的意思:假設今天是世界末日,然後你們來排演世界末日。這是你們表演的主題。但如果世界末日真的來臨了,你們誰也無法去作這個表演。但,如果世界末日還沒來臨,你就可以運用你的個人經驗來創作這個主題的演出。
或許,針對於史坦尼斯拉夫斯基關於個人生活與戲劇之間關係的觀點,人們總是可以提出反駁,例如傳統的東方劇場的演員們總是和自己的家人在一起,他們排練時總被他們的孩子和家裡的小雞包圍著。的確如此。馬戲團裡的情形與此相似。一家人組成了一個團體,這種情況比較特殊。但我們要記住,他們不是在扮演一家人,他們就是一家人:親生孩子、親兄弟、親姐妹。
生活展現著強而有力的事實:某位熟人的出生、死亡。這樣的事情震撼著我們的全身心。毫無疑問,如果我們真的能敞開自己,我們的社會面具會因此而在某一個時間被摧毀、被壓制。戀愛的時候也是這樣。但不久,人們便會重新拾起那些套路。經常性的,諸如此類的事情都是通過面具、套路得以呈現的。我不是在此抨擊這一現象,事實上沒有社會面具人們根本無法生存。這在某程度上是很「自然」的事。但我還是要表明,真誠——我們必須找到——為人類打開可能性的大門。真誠,與那些生活中強而有力的事實一樣,是完滿(complete)的。因為如果我們總是帶著面具、隱藏自己,我們就是在自我折磨,痛苦將一直持續到末日、死亡和瘋狂。在真誠的短暫瞬間——常常發生在最親密的關係中,關係的注定的對象不是任意的而是特定的,但不是任何時候都會發生——在這些不一般的時刻,我們才找到生存的動力。感謝這些真誠的時刻、完滿的時刻,感謝我們一直信奉的決定,只有它們才能證明我們的生命之路是正確的。我們若能在工作中找到真誠,在獨處的時候找到,在面對他人的時候找到,我們便會變成一個更好的人——即使只是直接了當地把自己的真實想法告訴他人。
你們之前作了關於囚籠主題的練習。我當時的印象是,演員們製造了一個巨大的謊言,很虛偽。一個囚籠,是和某種關押情境及體驗邪惡的經歷聯繫在一起的。所以我一直在觀察演員們會如何把受苦當成一種不尋常的、特別的東西來追尋,就好像生活從來沒賜予他們吃苦頭的機會一樣。當我看到一個演員帶著驕傲的神情,尋求用眼神表達悲傷、羞辱、悲慘等情緒,我得到了和他的期望完全不同的效果:我感覺很可惜,生活沒有給予他歷練和艱辛,我真的希望他能得到這些,因為他現在的表演簡直就是滑稽。像這樣自娛自樂很容易。你們在為人類的宿命尋找一種悲傷的、痛苦的、壓抑的、反思的氣氛。這總是讓我想起一個眾所周知的故事:一個可憐的處女,每天都在等待有人來把自己強暴。她會對那個男的說「我不要,我拒絕,永遠不要」,但事實上,她希望有這一天。不管如何,一個真正被關押的人,會找方法把自己的處境忘掉。他希望能適應,試著看看在囚籠中能否找到歡樂。而在當中尋找悲傷的人,必定是在撒謊。有些人帶著滿臉愁容唱著歌,有些人面無表情,另一些人念叨著難題或緊張地抽搐或眨巴著悲傷的眼睛。很明顯,這些表現都不真實。就好像你們在游說其他人相信你們在遭受痛苦,以此印證你們的吸引力。當然,有不少表演都是這麼做的,而觀眾們對此也很滿足,因為他們有機會在這樣的情境中施捨同情,以此顯示出自己的高貴。這對於演員和觀眾都毫無損失,對於雙方來講都是在心理上把自己隱藏起來,因為他們的生命沒有發生任何變化。第二天醒來,前一天的骯髒把戲依然會繼續。好吧,在演出的當晚,他們可以把自己顯示得高貴一點。
在前面的一場研討會上,有一個小夥子到這來,想表演一段對黑人充滿同情的獨白。他有同情心,但這對於黑人毫無幫助。他以這樣一種廉價的支持來表明自己的道義之心。他身處在這樣一類人群中,他們吃得很好、穿得很好,即便穿得不好也是因為想這樣穿。在此情境中,他不知羞恥地把自己放在烈士的地位,像一頭土狼、一隻禿鷹。他就在這裡,就在這個房間,顫抖著聲音,對自己很滿意。之後,我開始和他一起工作。我僅僅是強制他 更努力地工作——不是帶著痛苦,而是作出真正的努力,二者有點相似,但比受苦舒服多予。他開始掙扎。這沒有產生痛苦,而是讓他感到疲憊。只有到此時,他之前準備的那份獨白才具有了產生真實的苗頭,因為只有在不幸中人們才會反對不幸。在此情況下,人們不再炫耀他們的悲傷是多麼高貴。也許這個年輕人沒有方法去真正幫助黑人,但他為什麼要像個禿鷹一樣去吞食別人的不幸呢?我寧願聚集起最低限度的勇氣,去揭示直接觸動我的事情:什麼使我謙卑,我向他人隱藏了什麼等等。至少,這些都是誠實的表達。
今天,人們切斷自己與真正的根的聯繫,轉而尋找幻想中的根,就像他們做的所有那些虛幻的事情一樣。從不同的文化中尋找根是不切實際的:人們也選擇古代的、傳統的資源作為自己的根。我的意思不是說這些選擇都要被否定,相反,這些選擇可以作為跳板幫助我們尋得自己真正的根,但它們不能被直接用來填塞我們內在的空虛。我在筆記中這樣記到:「這種做法意味著人們試圖切斷自己與所有的根的聯繫,而事實上這只是想擺脫一切的義務與責任罷予。這是怎樣一種觀念?是一種簡單易行的、在成長環境中悄然接受的觀念。倘若一個人在這樣的觀念下談論‘社會背景’,那其實他還根本沒有思考過社會,只是在考量他自己周圍的一切。」
在X女士很清晰的發言中,我有一點不太理解:為什麼精英主義和創造性活動彼此不能相容呢?當然,從社會的角度來說,我們可以反對所謂的精英主義創作,可是我們能說里爾克( Rilke)的詩歌——無疑是為精英分子所寫的——就不是創造嗎?反過來,「牧女遊樂園」(Folies Bergere)可不是一個精英劇院,但如果你要說在那裡有什麼創造,那就太誇張了。所以,我不太明白精英主義和創造活動之間的關係。但我認為這裡有一個術語運用的問題,因為當你們說「主觀主義」(subjectivism)的時候似乎都必然包含著「精英主義」,但在現實中這是兩碼事。無論是艾略特(T.S. Eliot)的《荒原》(The Wasteland) 或者喬伊絲的《尤利西斯》(Ulysses)都不是純粹的主觀性作品,所以這兩部作品都包含著創造。如果事物是純粹主觀性的話,那它就不能引發創造,因為任何交流都不存在了。
精英主義的現象非常複雜。正如你們正確指出的,它與時間和環境相關。今天一些只被小眾——讀者或觀眾——所接受的邊鋒現象,可能明天就被普羅大眾所接受予。今天被人們普遍接受的藝術現象,明天可能一下子就消亡,其存在的功能就只變成如同可口可樂一樣。還有一種不同的、但並不簡單的可能性。例如,喬伊絲的作品可能至今仍然只為一小部分人所理解,但因為他打開了一些視窗,那麼大家都可以輕鬆地進入、作出理解。常常有這樣的情況:我們認為是小範圍的現象,卻製造了超出我們想像的大範圍影響。反之亦然:今天有些藝術家覺得自己的作品名揚四海,覺得自己的作品適合每一個人的,但其實沒人對其作品有真正的興趣……
我想回過來說一說主觀主義的問題。這是個很微妙的問題。譬如,我覺得「為觀眾而演出」是很危險的。我也認為如果演員的創造中沒有絕對的主觀性,那就沒有活力;但是,如果在觀眾們面前,這種主觀性不能轉換成客觀事實,那這就不是創造了。我再重複一遍,我的意思並不是不要「為了觀眾而表演」。關鍵在於,如果我們不自我欺騙,那表演就是客觀性了。但這是一件微妙的事。不是為了觀眾,而是與他們共同在場;不是不要主觀性,而是將之化為一個客觀的人類事實。這其實很簡單,就是我們在坦誠地工作,還是在作自我欺騙。
當一個演員面對觀眾而演出,他是把觀眾視為演出的有機部分。當一個演員希望為了觀眾而演出,他則期待笑聲和掌聲;這樣的話,他就會使演出過程變得虛假,他不會再努力地從自身中揭示出什麼,而僅僅努力去獲得觀眾的接受。在所有的創造——包括演員的工作——中,實現創造的媒介是人自己的生命。所以人們無法以他人的名義來進行創造。人只能展示自己的生命,所以創造必然是主觀性的。但有時人在欺騙自己的同時也會堅信自己很真誠。當觀眾在場,表演的中心變得客觀性,那麼就不大容易去欺騙自己。那什麼是客觀事實呢?關鍵不在於觀眾是否喜歡你的表演,而在於你的表演對他有所觸動。絕大多數時候,觀眾都對偉大的創造表示抗拒,但這恰恰表明他們還沒有麻木。這就是我所說的客觀事實:它在與觀眾的面對中形成,有自己的意義;它作為生命的一種事實而形成。觀眾可能喜歡它也可能抗拒它。但它就是一個事實。在這個意義上,沒有客觀性創造就不可能存在。把「面對觀眾而演出」和「為了觀眾而演出」二者分別清楚非常重要。觀眾接受一個事物,有時並不是因為它是一個藝術品,而可能出於其他原因。這就像「牧女遊樂園」的例子,人們接受那裡的女性舞者不是因為她們對生命有所揭示,而僅僅是因為「有意思」。觀眾會為某些蠢事拍手叫好,為那些對生命毫無啟示的表演——僅僅是模式化的重複——而喝彩。它們就好像餐館裡的餐後甜點,好像為了一夜風流而準備好房間,好像瑣碎的、搞笑的事情,今天我們會為之喝彩,明天就忘到九霄雲外。如果不是一個客觀事實,沒有人第二天還會想起它。它不會進入到他人的生命中。它不是生命的事實。
可以肯定,很多偉大的作品都不是由精英(elite)創作的或為精英而創作的,譬如圖騰作品。但我們得回答這樣一個問題:在今天,創作活動(creation)是否連一個精英都不需要,也不為了任何一個精英而創作?創作活動是否無需考慮時代的變化?於是第二個問題是,什麼是精英?如果你想到的是商業精英、知識份子精英,那麼他們當然不是能夠進行創作的精英。如果你想到的是人民大眾當中有著比常人傑出的才華的精英,那我相信我們離創造活動更接近了點。如果你們補充說,精英是具有較高創作性技巧的人,那我也偏好認為創造需要較高的創造性技巧——我對業餘不感興趣。亨利•盧梭(Henry Rousseau)沒接受過教育但他是一個技巧高明的藝術家。所以從總體來說,我認為「精英主義者的創造」這一提問是個虛假命題。
這個命題意味著什麼?為了精英進行創造?什麼樣的精英?有錢人?我想,為這些人進行創造並不是真正的藝術工作。除了少數例外,這些人追求的是生活中的而不是藝術審美中的事情。那麼是為了知識份子?為了那些有大學文憑、或者甚至是博士頭銜的人?在我劇院的觀眾中,我見過很敏感的工人,而大學教授們則愚笨得如門把手一樣。相反情況我也曾見過。為了什麼樣的精英?或許「為了精英」就意味著「不是為了所有人」。...因為,不好意思,我為什麼要為所有人進行創作?為什麼有些藝術家被迫要為我創造?這裡面存在著一個假設,即每個人都應該喝同樣的湯。
這是一種極權:每一項藝術創作都是為了所有人;這同時意味著,每一個人都應享受任何一項藝術創造。人各有不同,他們有不同的需要。藝術應當尋找那些需要它的人。如果它不是必不可少的,它就應該立即消失。一項藝術工作沒有必要服務於每一個人,它必須尋找到真正需要它的人。大街上的每一個人都能夠選擇出他自己的藝術需要。在藝術創作的領域,我想像著這樣一種民主:每個人都可以找到屬於自己的戲劇,每個戲劇都有自己的觀眾,戲劇就像人類一樣各有差異。不應強迫任何人去為所有人服務,因為這樣的話他做的一切都將被教條束縛。生命如此豐富,它的道路是未知的。一個藝術品今天可能有100個人需要,明天就可能有1000萬人需要。因此,藝術作品是不能不服務於人的。為了存在,它必須被人們需要。
我必須補充一點,即在過去幾個世紀裡,只有某些特定階級有選擇的權利。但過去時代中,特定階層的這種特權應該為大眾所擁有。如果你們取消了這個選擇權,你們就侵犯了人權。
有人說,如果整整兩周的工作,哪怕能經歷一件小小的具有創造力的事情,那麼時間也就不算白費了。好吧,我們可以說我們的確獲得了這種小小的收穫;你們應該感到高興,因為你們沒有浪費時間,你們都有這小小的收穫。但為什麼你們沒能收穫更多呢?這種對收穫的空談、對自身的要求在兩個星期的工作中是微不足道的——但這也就是我所說的「完美主義之路」:這是一種信念,它讓人們做一些很小、很小的事情,一步步地向前,或許某一天努力終有回報。
你們有人說,狗都會對撒謊的演員作出反應。我不太相信。但這個故事令我感興趣的是,它重申了我們的信念,並用狗取代了我的位置。如果不是葛羅托斯基在監督,那就會有一條狗來代替他。然而無論是葛羅托斯基還是狗,都無法完成任務。沒有人能夠監督保證別人是否真誠。
再回迷幻劑( LSD )問題。毒品的確能以某種方式讓人們敞開自我。然而觀察發現,它與創作工作毫無關係。這一點很重要。我們在此可以引用人文主義。但我們在吸毒中究竟找尋著什麼?不勞而獲。你可以稱之為自由。但有一些人使用毒品但同時也付出很多。酗酒的人也是同樣情況。但這是一種特別的情況,接近於一種病態,就像是陀思妥耶夫斯基(Dostoyevsky)的癲癇病,就像是梵高的(Van Gogh)的瘋狂——湯瑪斯•曼(Thomas Mann)曾注意到並分析了這兩個人的病態:他們和病苦鬥爭的同時也在創作著,所以,感謝這種鬥爭,他們的病苦漸漸造就了偉大的經驗。湯瑪斯•曼說,要感謝這些偉大的病人,他們以巨大的痛苦付出了自己的全部生命,使我們和其他人進入到往常不得涉足的境地進行探尋。當然,有很多癲癇病人,但只有一個陀思妥耶夫斯基。因此,只有在產出果實時,這才變得有價值。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前,波蘭有個演員,是個酒鬼。後來,其他波蘭演員都以他作為自己喝酒的藉口:「不管怎麼樣,傑瑞奇(Jaracz)也喝。」但傑瑞奇一直和酒癮抗爭。他常常讓奧斯蒂爾娃(Osterwa)把他關在房間裡,窗子釘上欄杆。到了晚上,他就試圖逃跑。他向外面街上的行人求助。如果有人幫他逃出來,他一般會說「去波蘭遊覽!」——然後他又會喝醉。回到家後,他再叫奧斯蒂爾娃把他關起來。這種自我抗爭中有一種英雄主義的精神。傑瑞奇創造出了精彩的作品,而大量的酒鬼和醉醺醺的演員們在排演中根本毫無貢獻。歸根到底,有很多事情和毒品的功能是一樣的。譬如我所說的「幻覺」,它甚至會引人自殺,一種可憐的做法。毒品的危險性也是如此:差劣地替代了一個本否可很美妙的經驗。
今天,我們在戲劇中常涉及性的主題。我覺得這沒什麼錯。相反,我覺得這很正常。如果不涉及到人類身體的性行為,戲劇將不可能呈現出什麼真理。但是,還有一個「狼來了」的問題。如果你在練習和即興表演中,在高潮情節和一般情節中,在身體練習、造型練習、聲音練習等所有情境中都在尋找性主題,這代表你想表現和強調這些主題,那你將使整個領域變得低級和尷尬。性主題的加入很快會變成一種程式化的慣例,你的真誠也因此被封閉。如果一個人希望徹底真誠,那他在性主題這個領域也必須真誠。否則,當你真的遇到危險時,再喊「狼來了」也沒用了,因為你已經把事情變得庸俗無聊。
在很多地方我都看到一個問題,那就是現學現賣的急迫心情。我很震驚地發現,有些曾經來訪問過我們、接受了一些訓練的人,如今在他們自己的表演中,居然把他們學到的訓練作為序幕向觀眾演示。當演員把個人化的動作、個人的拼搏都轉換到一種框架模式中去,以便向他人演示,這是很令人尷尬的。這樣的訓練就其本身而言毫無意義,是貧乏的、沒有活力的,是不知羞恥的。更不要說,這些訓練常常是以怎樣一種可悲的方式呈現給觀眾的。最大的危險是,什麼東西都被現買現賣。可是,就算我們不從道德角度而從效率角度來看這個問題,就算我們想如蛇一樣聰明、像狐狸一樣狡猾,我們也應該知道,什麼也拿出來賣是最容易令人喪失自我的。
名聲的狂妄。年輕藝術家的名聲,在一定程度上還能被辨識,因為總的來說其中還包含著一些人性現實。剛剛出名的年輕藝術家,如果在作品中克服了虛偽與惰性,其面目就可以通過作品清晰地展示出來。但兩三年之後,這些藝術家的面目都不再可辨了。怎麼回事?我知道怎麼回事。某種藝術現象強而有力地在運作,吸引著人們的注意力。開始的時候這種藝術家現象名副其實,藝術家的作品引起巨大反響。這時,一種旋風效應開始形成:但這個世界需要新奇事物,它很饑渴;於是大眾媒體加入進來,報紙、電視等等依次登場;藝術家的作品名聞天下,其名聲超出了它自身的價值;於是,反響不再是作品的反響,而是反響的反響我曾經讀到過某些烏拉圭人和印度人對我作品的描寫,但這些人從沒看過我的作品。這就好像兩面鏡子相對而放,鏡像作用十分巨大,但都只是幻覺。媒體的另一個重要特點是,它們總是期待著新鮮的事物。它們會樹立起一個偶像然後將其打倒,因為需要製造下一個偶像。
我想我們的作品,作為某種被崇拜物件,在數月之後就會被拉下神壇。即使不是今年就是明年,因為世界在期待著下一個新奇事物出現。媒體需要另一個新的預言家——他將坐在這,成為下一個焦點。
通常在一個人名聲鵲起的時刻,他會開始擔心他自己的地位。他開始考慮如何能夠持續吸引大眾對自己的關注,如何吸引更多的報導與電視出鏡機會,如何製造新的轟動,如何比這個時代更加現代。他開始去做並非出於真正需要的事情,他小丑般地在媒體面前手舞足蹈。他所做的一切都只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所有這些,就是他毒害自己、消滅內心活力的開始。或許,以此方式他可以為自己贏得一兩年的虛幻名聲。然而,最終他仍將被棄之路邊:被利用殆盡,毫無尊嚴與真誠;被殺死,變作一副屍首,充滿著對新偶像的嫉妒之心,充滿著邪惡的信念和報仇的願望。這時,其面孔漸漸消失迷糊了,再也不見往日的光彩。
從演員的情況來說,這一切開始於他不再專注於自己的工作。為了保持自己的優越地位,演員需要做千百件事情:在劇院裡演出,在別處演出,與公眾見面,毫無準備地在電視節目中秀一把,參演電影。他贏得了大眾的關注。通過這種方式,演員比導演能夠贏得更長時間的關注。但是他很清楚自己已經死了,於是開始不開心。這一切都開始於那種偽君子式的把一切都拿去販賣的舉動。
有沒有可能不去販賣?我們可以反對潮流,可以不在乎媒體的吹捧。這完全可以。那我們會被攻擊嗎?會的。但相比之下,我們的偶像過不了一兩年就將被掃除。這是唯一的區別。而事實些偶像的光環被打碎比沒被打碎的好,因為我們應該知道,心中沒有真理的種子我們就不會快樂。不快樂的原因就藏在自己的心中,是我們自己在折磨自己。這種折磨源於一步登天的欲望,源於工作就是為了成功、為了名聞天下這一想法,源於將自己獲得的一切立即出賣的舉動。之後我們會問自己為何如此緊張。我們責怪大都市造成了這個局面。但如果說是大都市對我們產生了負面影響,那也是因為我們居住在其中。所以顯而易見,第一件我們可以做的事情就是離開大都市。沒人會強迫你在巴黎工作——你可以到鄉郊工作,到一個小鎮上工作。你在那些地方就不能做戲劇嗎?你能。我就不在波蘭的大都市裡工作,也不需要華沙給我的名聲。弗羅茨瓦夫(Wroclaw)就比華沙差嗎?我喜歡那個城市,那裡的人們需要我。為什麼要到首都去?如果你們不喜歡紐約的話為什麼要待在這兒?
當然,如果我像喜愛故鄉一樣喜歡華沙,我會去那裡。如果我喜歡紐約,我也會去,那時我就沒有權利再指責紐約的氣氛讓人窒息。如果實在不能忍受,就搬到三藩市。也有一種可能,即在紐約工作,忍受著它的噪音和其他種種,但保持自己不受影響。可是如果紐約讓你害怕安靜、不甘寂寞…你會想著「哦,今天有人寫了一篇對我不利的評論,我必須在電視上回擊」、「沒有新的轟動我們就完了」等等。經濟壓力當然存在,但我認為這不是決定性因素。我不認為這些內在躁音必然是賺錢的代價。是的,這些是必然的,但只是為了賺更多更多的錢。但你自己究竟想要些什麼?可能你想要的是錢而不是其他。你必須認清自己想要些什麼。如果不是為了錢,那你將有更多的自由,比如不再受制於媒體。我不反對適當使用一些媒體宣傳策略,這方面的壓力的確存在。媒體宣傳中我們應保持機敏。但媒體策略決不能干擾到藝術工作本身。工作之外,媒體策略可以搞得有聲有色,但二者孰重孰輕不能混淆。一旦混淆,藝術工作將走向貧乏。這種例子隨處可見。
隨處可見的還有另外一類事情,即一種創建技巧的特殊方式。我舉個例子。某個人曾和我們一起工作過一段時間,並學習了我們的造型練習(plastique exercise)。他離開後一直在家鄉做這些訓練。後來他堅持說自己已經發明了一套做這些訓練的新方法。我們只能對此表示尊重。但是,當我到他那裡訪問時,我親眼目睹了他所說的新方法。所有簡單的部分都保留下來了,所有難的部分都被放棄了或者難度被大大降低。我們在此經歷了雙重假像:第一,他製作了一套他自己的、創造性的訓練方式;第二,練習中所有動作都在包含內。事實上,這種行為背後的目的源於自我虛榮。對於此個案,我們可以說自我感覺良好更勝於訓練本身。那麼整個訓練過程是沒有生命力的,甚至可以說,訓練從來沒有開始,因為這種訓練根本就沒有內在的過程。
現在我們可以看到到處都有一種趨勢,即將自己和傳統割離,卻又沒有和傳統的弱點割離。這些到處都能看到,人們在無根的狀況下試圖進行創造,在與過去毫無聯繫的情況下創造「新事物」。確實,我曾多次重申,一個人需要「獨立」(independent) ,但總會引來一個疑問:這是一種真正的自主(autonomy)嗎?或只是自主的另一種替代?舉個例子,如果這不是源於自發性——一種演員的本能——我觀察過一種人們稱為「瑞典式體操」的運動,但其中毫無新意,實際上只可稱為「瑞典式懶惰」。從理論上說,這是一個自主的例證;從實踐上講,這套體操的編排水準非常業餘。你必須清楚你在做什麼。我們實驗所劇場創造出的這些訓練動作並不重要,你們可以有自己的動作組合。但不管什麼訓練動作,都必須細緻而準確。要麼你們從一開始就尋找自己的訓練方式,要麼就跟著我們的套路學習。但不要在還沒有完完全全學會之前就實驗自己的方式。要先做好,才去創作自己的版本。在訓練中需要培養自制力。當陷入混沌狀態、隨眾聲喧嘩,或進入恐懼,變得馴服,這些都是缺乏自制力的表現。你不應在這裡混入一點身體練習、混入一點造型練習、混入一點聲音練習,但當中卻沒有一點是你自己創立的東西。不要將所有東西混在一起攪成一鍋粥,然後感覺良好地稱自己為創造者。
我們絕非割裂於周圍的環境、國家和傳統——它們是力量的泉源。只不過我們與這些源泉的共在需要各種不同的外在表達。我們總是根據個人需要去追尋幻像——而非國家民族的需要,當然有例外。但表達的方式一般總是民族化、國家化的。這說明,我們的自我保護本能強迫我們在行動中與周圍環境、主流生活方式等保持一致。所以法國人會推崇笛卡兒的言論、北歐人會推崇信賴感都是很自然的事。這些都是基於特定的社會背景。根據模仿的法則,國家、民族的價值觀必然投射到到個人的行為表現中。
人們問,我的意思是不是要除掉所有的面具,包括文化的面具、傳統的面具等。不是的,這與「除掉」無關。整件事始於我們是否覺知自己有著面具。我們無法毀掉面具,它有點像我們的皮膚,它可以被撕下來,但不久新的肌膚又會生成。然而,有些時刻,當我們會放下自己所有的防備時,面具之下還是會長出不一樣的東西。
某程度上,藝術是不道德的。人們只著重成果,而忽視美好的原意。當一個人在工作時屈服於幻像時,那麼就只是在工作著幻像。相信我,我也希望這不是事實。
在劇場中,如果我們想超越獵奇(anecdotes),我們必須找尋一個連貫的架構,而在架構內我們和我們的生命經驗去揭露自屈。那麼故事就只是一個載體。你可以說它成為了燃料。
這將會變成一個心理性的現象。或許我們需要考慮心理(mental)、知識性(intellectual)跟精神(psychic)不一樣——這些只是精神的一部分。這一點會引起疑惑。當我說淨化(purity)可以超越這個界限,這恰好淨化是關於精神層面的。
我想對Y先生說些話。我想說我不相信自我批評,因為有些極度危險的東西在當中,尤其是在某些情況中。我的意思是,一個人可以扮演、或是做一些手勢去表達他正在毀滅自己。當大家都理解,就不再需要語言。
這是否沒有人性?是的,你可以這樣說。除了在這裡提及過「人文主義」的另類選擇道路外,我認為人類是非常不開心的。這都寫在他的臉上,寫在他的生命上,寫在他的反應上。而他還未獻祭自己…
當我看到訓練不能奏效的時候,我有兩條路可以選擇。我可以說練得不錯,但是我更看重其他某方面。可以肯定,這樣就把你們拉到了我的軌道上,而所有的事情將繼續拖延下去。但我意識到,為排練負責的應該是你們自己而不是我。我也可以對你們說,有些部分做得不好,但某方面做得很好,所以你們並沒有浪費時間;這樣,你們依然會尊重我並且依然「感覺良好」。但我便需要為延長了這個錯覺而負責。所以我只能選擇第二條路,即抹去你們心目中的葛羅托斯基,讓你們對我感到厭煩、討厭。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責備都將與我無關,我只是在履行我自己的職責。
在研討班的活動中,你們已經注意到,我的確以某種方式缺席。我僅僅是在觀察著一切的發生,因為我打算履行我自己的職責,去面對我的訓練所出現的各種各樣的錯誤印象。即使我來到這裡,想和大家交流,但我對於交流的內容與方向都沒有預設。這些都是我需要的。如果曾經有一個偶像,現在大家都看到,它已經被打倒了。毫無疑問,對偶像的崇拜不會再繼續下去。也正是出於這個原因,我在排練中不能回答你們的問題。一個小組在擁有了多次膚淺的、表面化的經驗之後,會煥發出真正的活力,這時常會發生。我一直等待這一刻的出現,直到研討班的最後一天。
有人會認為我不是一個有信仰的人。那麼,把你們的真我展現給我,我就向你們展現我的上帝。
是時候結束了。或者還沒結束?我建議就此結束,我不打算讓組織者再來作一個模式化的總結,就讓這次聚會有一個開放的結局。如果有人還不想離開,讓他留下吧,讓他做他想做的。